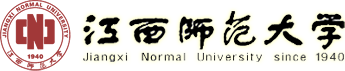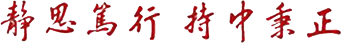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会有一些人被历史“选择性短期遗忘”。胡先骕,无疑属于这一类人。
作为20世纪江西诞生的两位顶级学术大师之一(另一位是陈寅恪),胡先骕这个名字,很长一段时期鲜为人知,了解者更是寥寥无几。
5月24日,一场隆重却并非盛大的胡先骕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在江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和胡先骕的亲属代表共聚瑶湖之畔,深情回忆了这位被誉为江西高等教育界共同的“老校长”的伟大精神与人格魅力。
在一段段充满温度的史料与讲述中,历史厚厚的封尘渐被拂去。胡先骕,这位集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于一身、坚持追求真理与守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大师,其鲜活的面容一点一点还原在世人眼前——
有人说,他是“开创者”。因为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曾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也有人说,他是“守旧派”。因为他曾作为《学衡》主将,与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胡适等人大开笔战,共同书写了20世纪文化史上省略不了的一页;
还有人亲切地称他为“江西的老校长”。他曾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40年,回乡创办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正大学,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约请了一大批在外的江西学者回归乡梓,设坛讲学,培育了一大批人才。
无论人们如何评说,无论胡先骕具有怎样多重的身份,无论他曾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过怎样的角色,都不能影响他的当之无愧的身份——大师。
■“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他是坚持真理、追求科学的植物学家
5月23日一早,大雨刚过,庐山植物园内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胡德焜带着家人静静地伫立在父亲胡先骕的墓碑前,良久。年近八旬的胡德焜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神情。是哀思,更是感慨!“父亲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与那个时代相关,更与他专注、执著、耿直的性情有关。”
1894年,胡先骕出生在新建县治平洲胡家府宅。家学渊源深厚的他,自小就显露出了极好的天赋。5岁课对,7岁作诗,12岁参加科举,15岁入京师大学堂,18岁留学美国学习植物学。
作为幼子,胡德焜说自己和父亲的交集似乎特别少。
“记忆中,他是一位温和的父亲,从不打骂孩子,甚至说话也不大声。可是在做学问上,他却是一个极其认真、甚至有些严苛的人。时常为了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而变得亢奋,或是跋山涉水,收集标本,或是通宵达旦,研究资料。”
1916年,在美学成归来的胡先骕,受聘为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后转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植物学教授。这一时期,他先后两次到浙江、江西,踏遍两省境内的崇山峻岭,采集到大量的植物标本。并与同事共同编著了《高等植物学》一书,这是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现代植物学大学教科书。
1922年,他在南京创建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并任植物部主任。
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增设生物学系。这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学系,28岁的胡先骕担任系主任。同年,他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两年后获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
翻开《赣鄱科技名家》,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胡先骕身上有着许多“中国第一”:
1915年发表论文《菌类研究方法》,是中国最早的有关菌类的论文;1925年,由他命名的兰科风兰属,成为中国人科学命名的第一个属;1934年创建中国第一座大型的亚高山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1948年,与郑万钧教授一起首次鉴定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成为“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植物学界最重要的发现”,他被誉为“水杉之父”……
对科学专注的胡先骕,一生共出版21部专著和译著,撰写了150余篇论文,涉及植物学、文学诗词和教育等领域。在群星闪耀的20世纪中国文化星空,作为植物学家的胡先骕无疑是熠熠生辉的一颗。
曾有人疑惑,当初年少的胡先骕赴美留学,为何会对偏冷的植物学“一见钟情”?庐山植物园研究员胡宗刚在《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中回答过这个问题:“他曾在致胡适的书札中阐述过选择植物学的原因——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而后,又在名为《书感》的诗这样写道: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好一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原来从起点开始,胡先骕早已将自己的选择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矢志不移。
■“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他是持中秉正、坚守传统文化阵地的人文主义者
“由于过去一些文学史教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胡先骕在许多人印象中是白话文的反对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但现在学界已经认识到他只是反对当时的一些极端做法。”面对那场已逝去近一个世纪的“文化笔战”,原江西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傅修延教授直言道:“与其说胡先骕是站在反对立场上,不如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诤友,是敢于直言、指出不足的真正朋友。”
伴随傅修延教授的讲述,我们再次打开尘封的历史。
1919年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针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判传统的运动,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挺身而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向“北大学派”发起反击,形成了与北方对峙的南方“学衡派”,其主要成员就有胡先骕和他的同学吴宓、梅光迪等人。
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对胡适的改良之说提出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结合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阐明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另一篇则是《评<尝试集>》,胡先骕花了20天写出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以中外文学的史实和理论,批驳了胡适新诗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
“二胡”之争一时“硝烟弥漫”,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二胡”之争被定性为进步与保守的差别。然而,经过近百年的时光淘洗,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要,如何建设新文化?
“和新文化派相比,胡先骕带领的学衡派认为文化演化是一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过程,新旧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绵不断的传承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说道。
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当年的胡先骕“持中秉正”的可贵。江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叶青说:“胡先骕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真诚而严肃的思考者。或许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形象。但他的思想绝不凝滞。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精神是十分深刻的。”
■“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他是唯才是举、术德兼修的教育家
如今,人们谈论起胡先骕,更多地会关注其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这与他曾是江西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大前身)的首任校长密不可分。
胡先骕爱才是出了名的。创建初期的国立中正大学,条件简朴、生活艰苦,作为校长的胡先骕却竭力延揽人才,先后聘请蔡方荫、俞调梅、戴良谟等大批名流学者前来任教,其中不乏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博士,一时名家毕至、学者云集。据统计,当时的国立中正大学有教授78人,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大学中,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这样的排名,至今仍令江西高等教育界叹为观止。
爱国教师姚明达一行不幸与日军遭遇,最后中弹牺牲。胡先骕率领全校师生恭迎烈士灵柩,灵车抵达,他抚棺失声恸哭,亲自写挽联悼念;1943年,杏岭伤寒猖獗,数十名学生感染,他积极奔走请来全省最好的医生,购买最好药物;同年,他还顶住巨大压力保护砸《民国日报》社事件中的学生,与当局发生正面冲突,终请辞校长一职。
如果说爱生如子、唯才是举是胡先骕作为教育家的情感向度,那么以德为先、术德兼修就是他教育思想实施的具体抓手。越过数十年的沧桑,在他的《精神之改造》等文章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对现代大学教育目的的深远思考。
他提倡教育独立,反对专业训练,主张“术德兼修”“尤贵宏通”;曾公开主张通才教育,说“学校不应该让大学生的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应该让他有自由选修课程、自由研究学问的机会。”这样的观点,放在今时今日,同样是高等教育者应该执守的。
■“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他是率真可爱、有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
纪念研讨会上,一位专家讲述了这样一段史料,令人记忆深刻:
“据中正大学学生回忆,开学典礼上,胡先骕‘身着马褂长袍的中装礼服,鼻梁架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上唇还蓄着一小撮希特勒式胡须’,对同学们说:‘在国外的知名大学,如牛津、剑桥,学生们是很难见到校长的……今天,诸生能够如此轻易地见到我,这是你们毕生的荣幸。’”
无独有偶。后来,胡先骕在广西大学演讲时,也有这样一段“自负”的开场白:“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演讲,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
听上去,这样的胡先骕似乎“有些自负”。可这样的话语,恰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自信与率真。
正是这样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矢志不移。胡先骕的学生陈心启回忆说,先生和日本天皇是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东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又是他在学术界的老朋友,抗战爆发后,后者曾亲自来华,劝他为日本人做事。铮铮铁骨的先生不仅毅然拒绝,更是放出豪言:“日本没什么了不起。日本天皇就是我的同学,他的学习成绩不如我。”
也正是这样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听了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广的学术报告后,毫不留情地说:“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敢于拒绝蒋经国邀其将中正大学迁往赣州的要求,从而激怒蒋经国;敢于对蒋介石的庐山约见“不买账”,漏夜下山;还敢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学术界一边倒的形势下,独树一帜,公开严厉批评当时红极一时的前苏联李森科学派“是伪科学”。
“为科学而科学”,是这样一位从“五四”时代走过来的、坚持“民主与科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一生的座右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早已成为他血液里流淌的一部分。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历史对他的选择性遗忘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为了传承的纪念
连日,在采访了众多与胡先骕先生有着这样或那样“关联”的人们后,作为一个整理者和记录者,记者的心始终没有平静过。
这是怎样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巨匠大师?能如此轻快地游走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领域,如此执著、简单地追求理想、坚守信念,如此率真、可爱地保留着一位独立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
有人曾说,这样的胡先骕,注定是一个孤独的“另类”。而记者却以为,这样的胡先骕,恰恰是从“五四”时代走过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集体影像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曾经是相携相知的朋友,还是激烈争论的对手,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独立人格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他们大多知中晓西、熔铸经史,是开宗立派的先行者和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他们的知识底蕴、文采风流、人格魅力,在21世纪的今天,在经济大潮汹涌,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甚嚣尘上的当下,是多么可贵的一座高峰。
然而,身处当下的我们,面对先贤,除了短暂的回眸与纪念,还能做些什么?作为胡先骕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的“操盘手”,江西师大副校长张艳国道出了他的理解: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如此隆重地去纪念胡先骕先生,不仅是要怀念他,要挖掘和整理他的思想和成就,更重要的是传承,利用好高校传播、教育的功能,让更多的青年一代走近胡先骕、了解胡先骕,继承他坚持真理、追求科学、执著理想、救国在己的崇高精神和学贯中西、兼容并蓄的治学思想。同时,作为教育者,秉承胡先骕唯才是举、术德兼修的教育思想,办好一所在江西引领文化高地、精神高地、风尚高地的现代大学。这是我们纪念的目的,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链接:http://epaper.jxnews.com.cn/jxrb/html/2014-06/06/content_245182.htm